清人沈太侔《春明采风志》记载:“凡年终应用之物,入腊,渐次街市设摊结棚,谓之蹿年。如腊八日前菱角、米、枣、栗摊。次则年糕、馒首、干果……太平鼓、响壶卢、琉璃喇叭,率皆童玩之物也。买办一切,谓之忙年。”可见当年北京过年内容之丰富。
明人袁于令写《隋史遗文》,交代主人公秦叔宝在一番“卖马当锏”的惨淡际遇后,客居在潞州好友单雄信的农庄,“到了除夕,雄信陪叔宝饮到天明,拥炉谈笑,却忘了身在客乡。叔宝又想着功名未遂,踪迹飘零,离母抛妻,却又愀然不乐。”秦叔宝日后与战友尉迟恭一起化作门神,走进千家万户,几乎成了春节最重要的符号。但《隋史遗文》是叙述秦叔宝未遇时节的小说,这番过年景象,恰如宋人苏洵的诗:“佳节每从愁里过,壮心时傍醉中来。”
无论欢乐还是乡愁,无论新景还是旧诗,在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留下的历史记忆里,人们更多看到的还是一种沉淀下来的感情——特别是在除夕夜,在这个时空交错的特定节点,故乡、亲人、未来……常常混合成一种奇妙的领悟与感动。
相比起来,当代人往往会有一种“年味淡去”的感觉,不少人为之伤感,认为伴随现代文明而来的快节奏与物质化,冲击了本该更加温润的心灵世界。
“这种感受比较普遍,问题是怎么看待。”北京大学民俗学教授陈泳超说,“随着经济条件提高,春节原先负载的‘非同寻常的物质享受’功能,自然会‘领土尽失’。‘年味淡薄’主要是在心理层面:人们每天生活越来越相似,反而失去了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和原先春节带来的高峰体验。”
陈泳超说:“我建议多回头看看、学学传统节日习俗。比如除夕团聚守岁,那是血缘关系的温情展示;比如拜年,那是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得以温习的大好机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不就这些吗?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些节俗是传统中每个人体验自己社会性存在的行为艺术。当我们用心去体会那些细节时,我们自然会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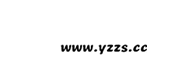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