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于网络
隔壁的公鸡开始打鸣了,曙色在不远处的江边洇开几抹胭脂红,在220年前的仪征城南大码头的河西街,45岁的萧娘醒得比鸡还早,她没有时间梳妆,忙碌使她习惯素面朝天,几缕花发被汗水紧贴在额前。对于30年来被别人喊作“美人”,她并没十分在意,她满意自己有一双勤快的手,她做的糕点、蒸饺、茶食满仪征城都在夸奖。而这个早晨尤其和往常不一样,有个年逾七旬的袁子长先生(注:袁枚)派人订下了3000套8种花色的点心套餐,说是专门送给江苏巡抚奇中丞的,来人千叮嘱,万招呼,一定不能马虎,提货的船就在大码头通往长江的老闸口等着呢。萧娘暗自惊喜,这是她独自掌柜以来接到的最大订单,可她又感到好笑,这点心,哪像街面上传的那样有什么祖传秘方和独门绝技,其实你只要把自己的一份真心放进去,再普通的食物都会做出纯正的味道。
作为独生女,萧娘天生有一双葱嫩光滑、白玉般的灵巧小手,抚过琴,下过棋,也学过女红,她本可以养尊处优,享受另外一番无忧无虑的生活的,因为父亲开的点心铺已小有名气,日子正往火红里过。可邻居一场意外的大火殃及了全家,父母葬身火海,一介书生的丈夫也落得个手残脚伤,她只能用一双纤纤细手,艰难地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和承继父亲传下的行当。
萧氏糕点的店幌重新活泼地晃荡在晨风里,撩痒了不少行人的眼光。食客们品着品着就品出了一番不同以往的味道。萧娘做的点心不仅洁白中看,小巧玲珑,而且舌尖上、口齿间总会留下说不清的缕缕暗香,这背后的变化只有萧娘明白,原料除了大米、糯米各自掺半,还糅进蒸熟的山药泥,这样可以软而不塌,黏而不腻;至于果泥、瓜子、松子仁、红绿蜜饯都必须经过她自己咀嚼一下,没有杂质和异味才能用于辅佐配料;升火用的是稻草、麦秸,还有从丘陵山区收集来的松枝、松针,那种山野的幽香借着火苗的烘托,蒸笼的热气,润物无声,潜入了点心之中,化作了贴胃贴心的暖暖气息……萧娘所做的这一切,都非刻意也非创意,她只是把自己平时听到的、看到的一些好的做法加以归纳、综合运用罢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
现在,萧娘的好运渐渐来了,许多有头有脸的人物,做官的、经商的、扬州的、金陵的,都来批量订货,小小的河西街常常被挤得水泄不通,大码头一天到晚闲客不断。一些文人墨客过来,并不真的都想品尝一下美食,“萧娘有多美?!”这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你看她那双大眼睛,朝你一眨,魂就被勾去了”,“那皮肤嫩白呵,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她近五十岁啦?三十岁还差不多”……这样的话,无疑是把萧娘当作秀色可餐的糕点了,她听了暗喜,心里一年四季撒满了快乐的种子,开满了春天的花朵,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会打上热毛巾为手脚俱残的丈夫洗脸抹嘴,她要向那些风流才子传递明白无误的信息:要多订些糕点可以,别想在萧娘身上打歪主意。
连续几个昼夜的忙碌,通过七八十个师傅的协力,袁先生订的3000套糕点终于备齐了,几十个挑夫接长龙似的向着不远处的老闸口移动着,没几天袁先生就收到江苏巡抚对萧氏糕点赞誉有加的诗词,著作《随园食谱》的袁(枚)先生自然心花怒放,食单中自然又多了几行文字:“仪征南门外萧美人喜制糕点,凡馒头、糕饺之一类,小巧可爱,洁白如雪。”
袁枚用萧氏糕点馈赠江苏巡抚并获赠诗的消息很快就在南京、扬州一带传开来,比袁枚小11岁且在仪征乐仪书院任过山长(教授)的大才子赵翼也心旌摇荡,竟然一口气为“萧美人点心”作了六首诗,对萧娘的美色美食不吝美言,可惜其时赵才子有些落魄,既无缘和美人亲近,也没能与美食碰面,最后只好哀怨“流涎馋煞老饕牙,只送侯门忘我家。题罢支頣聊一笑,纸窗风雪嚼梅花。”
自古夸奖美人,多有“倾国倾城”一说,而今人从史书中能集录到的专门颂扬萧美人点心的诗作就有10首之多,像袁枚、赵翼这两位在乾隆时期的三大诗家中占其二的重量级人物(另一位蒋士铨),心甘情愿为萧娘全心背书,留墨扬名,那岂不意味当时诗坛的三分之二江山为之“倾心”了?让人钦佩的是萧娘嘉庆元年(1796年)53岁那年去世后,除了萧美人点心,民间竟没有一星半点的绯闻传言,这和后人提起的另一位清初中国女名厨、秦淮名妓董小婉不同,她身前“白茫茫”的一片,倒仿佛坚守着洁白如雪的点心质地;她身后没竖起“中国第一女白案”的牌位,又好似她从没来过这个世界。凑巧的是,她走后的第二年,慧眼识她的袁先生也诀别了他的随园和美食世界。
时隔200年,有人在仪征的淮扬茶楼看到萧美人糕的食谱,真亏有心人将它记住。可萧美人糕与萧美人从来是不可分离的,所谓物以人传,萧美人早就化为留在白纸上的十几首黑色诗行,萧美人糕还能在城南还魂归来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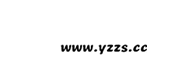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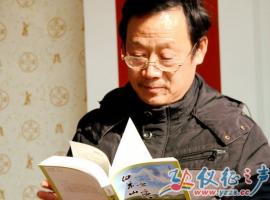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