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华
五叔说这个年他过得不开心。随后又补充说是相当不开心。 五叔一向是乐观的,无论什么烦心的事,一支烟的光景,就清清爽爽了。据说早些年家里穷孩子又小,四张小嘴张着要吃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五叔家一个咸猪头就能过个年,他依然是笑呵呵的。这些年,村里公认的最有福气的五叔,怎么反倒不开心了呢?
五叔说,让那几个孩子给气的。
五叔的孩子是全村最有出息的孩子,也是公认的很孝顺的孩子。怎么会气得五叔大过年的“相当不开心”呢?说是孩子,是针对五叔而言,其实最小的“孩子”也成家立业了。
一切似乎都是因为过年引起的。
前些年五叔自己家里养着猪,进了腊月门就请人上门杀掉,先把猪头腌起来,过年的时候拿出来炒菜。其余的,凡是猪的身体,都拿到集市上卖了换钱,给四个儿子添衣或开学时缴学费。现在倒是不用为孩子的衣食担扰了,四个儿子个个长大了,且都有了出息,两个在省城当官的,一个在邻市做生意,做得还挺大,一个在本市当老师。
孩子们都有了出息,早就不让五叔劳累了,更不让他再养猪了。五叔再也不用自己养猪了,但过年的咸货还是要腌,原材料到集市上买回来,一年比一年腌得多。自己是吃不了多少的,主要是让城里的儿子带走。官再大也得吃饭不是?工作忙了,顾不上炒菜的时候,切一刀下来,蒸一蒸,有滋有味呢,五叔说。
说起这个腌年货,是当地老百姓过年的一个特色。老一辈留下来的饮食习惯,一年一年地,就沿袭到了今天。进了腊月门,各家各户开始腌制“年货”,也就是说把一些生的肉呀鱼呀的抹上盐巴腌起来,腌好了然后再晾晒,然后再收起来,有冰箱的放进冰箱,没有冰箱的时候就放在背太阳的阴凉处,过年时拿出来吃。过年吃不完的,开春后还可以吃一阵子。当年我刚来到这座小城时,进了腊月,走在街上,到处挂着一串串的香肠,一嘟噜一嘟噜的猪下水,胖乎乎的大猪头,还有一条条被剖肚开膛的鱼……很是好奇。当地居民说,那是各家各户晾晒自家腌制的“咸货”,“咸货”上了墙,年味就来了。
五叔的儿子委婉地提出过,不要再腌什么猪头、猪腿了,一层一层的盐往死里抹,腌出来的肉除了狠命地咸,还是狠命地咸。再说了,城里人都讲究营养,讲究吃个新鲜,谁还稀罕这些用盐巴沤出来的肥猪肉呀。但是看到老人掰着指头数着几只猪头、多少串香肠、多少条咸鱼时的欣喜与满足,又是那么积极地往各家的行李包里塞着,儿子们把到了嘴边的话生生咽了下去。母亲不在了,老爸一个人也不易,这大过年的,别惹他老人家不开心,万一郁闷起来,生了病,那可怎么好!于是便不忍心打击老人的积极性。
于是五叔腌的年货里三层外三层地挂满了阳台。
去年那个挂猪头的绳子断了,那个胖乎乎肉嘟嘟的家伙一下子砸到了正从楼下经过的邻居新媳妇身上,砸得那个如花似玉的新媳妇“哎呀哎呀”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二后来才知道,人家那新媳妇正怀着身孕,我的天哪,这万一把人家的胎儿给……不能想,不敢想了,当儿子们回来过年得知这个消息,都倒吸了一口冷气,都是场面上有头有脸的人物,这老爸万一在家里惹出个什么祸来,这麻烦就大了不说,人家说不定还以为儿子们不孝顺,个个住在城里享福,单是把老爸放在乡下受苦呢。于是,五叔是继续留在乡下还是跟儿子进城的问题成了今年这个春节研究的头等大事。 当老大把这个问题跟几个弟弟一说,都争着让爸到他们家住。谁知五叔一口回绝了,我谁家也不去,就老死在这老屋里。
按理说,几个孩子都是孝顺孩子,这一点五叔知足着呢。但不去归不去,每年五叔都要到城里的孩子家住一段时间。这个很重要。或一个月或两个月,每次穿戴得新崭崭地红光满面地回来后,五叔都要到大队部去转一圈,因为大队部的院子里人多,打球的,下棋的,聊天的,都有。
五叔一出现,就有人打着招呼,五叔,好久没看到你了。五叔就说,噢,到省城住了些日子。声音不高,还故意用两声咳嗽声压了压音调,但里里外外透着两个字:满足。有人又问,省城很好玩吧?五叔说,嗨,有什么好的,除了楼高,就是人多。说着就掏出了软包装的中华香烟,撒了一圈。于是就有老伙计拍着马屁,咱这方圆几十里,谁最有福气,当然是五叔;谁家的孩子最有出息,当然是五叔家的孩子。抽了人家的嘴软,但也真的有感而发。
哪里哪里,五叔直了直腰,伸了伸腿,很自然地一双锃亮的棉皮鞋就被大伙看到了。五叔轻描淡写地说,老二媳妇给买的,一千多呢,哪有咱家的棉鞋舒服。说是这样说,只要是正式场合,比如到大队部转转什么的,五叔脚上肯定穿着它,于是,五叔那本来有点外八字的脚,立马就比平时周正了许多。
如果到城里常住下来,时间长了,谁还记得五叔?五叔锃新的棉皮鞋给谁看?再说了,到城里去,周围全是城里人,谁还用羡慕的眼光看五叔?人家不把你看做乡下人就是看你儿子的面了。所以,五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城里,可以偶尔去住,但不可以常驻。
三
乡下兴正月初一给长辈拜年。这里说的拜年是真拜,并不像城里人“拜年”,走走形式,说几句“过年好啊”就算拜年了。乡下人拜年是晚辈给长辈磕头。五叔在村里本来辈份就大,再加上五叔有四个有出息的儿子,子贵父荣,五叔在村里德高望重,每年正月初一来拜年的就特多。一般人家,晚辈来了,磕过头后,主人给男的敬支烟;给女的端出瓜子点心什么的;孩子呢,就在新衣服的口袋里塞一把糖,然后呼啦啦就到另外人家去继续拜年了。几乎没有留下吃午饭的。
而凡是五叔到家里来拜年,无论大人小孩子,一律被留下来吃饭。这就苦了那几个儿媳妇。儿媳妇都是腊月二十九或三十才回来的,回来后还没歇过来,大年初一就得挽起袖子下厨房为乡邻做菜备饭。一般都是十几个人,最多的时候二十三个,两张桌子坐不下,还有三个孩子就蹲在门口捧着碗吃。
刚嫁过来时,媳妇们以为当地就是这样的风俗,后来发现,左邻右舍都不是这样的,唯独公爹家这样。并且,渐渐地,媳妇们看出来了,公爹留大家吃午饭,是为了显示自家与众不同。
吃顿饭倒也没什么,问题是,人家那些拜年的人并不太愿意留下来吃这顿饭。都想赶紧地去别人家拜年,然后回家补上昨晚守岁耽误的觉。完全是碍着五叔的面子有些无奈地留下来的。一方面要以牺牲媳妇们初一整个上午的时间,一方面人家又不太愿意,这陪了夫人又折兵的事,何苦来着?媳妇们不干了,分别向自家爱人也就是五叔的儿子提过抗议,无奈,儿子们尽管心痛媳妇,但他们都是五叔的好儿子,只要老人高兴,老人怎么做都是对的。媳妇们没有得到丈夫们的同情,反而被灌输了一番要理解老人,要孝敬老人之类的大道理,心里都很不爽。
于是,儿媳妇们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
大年初一,儿子媳妇们给左邻右舍拜完年,老三媳妇给五叔端过一杯茶,笑容可掬地说,爸,我来的时候匆忙了,有些自己用的东西没来得及带。吃过饭我想让妯娌几个陪我到城里去买,您看行吗?
老人跟孩子之间也是有缘的,尽管都是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儿媳妇,但老人不同程度地也有偏爱。在四个儿媳妇中,五叔最满意老三媳妇,没有来由地,就是看她顺眼,说话,行事,都得体。当然了,最关键的还是老三媳妇最孝顺,去年五叔胆襄炎发作住在省城医院开刀,老三媳妇请了假服侍了一个月,那个尽心,那个孝顺,外人见了,倒像是自家女儿。
去吧去吧,五叔忙不迭地说。
按说,大年初一,五叔是不准孩子们离开家的,但是人家媳妇要去买“自己用的东西”,这做公爹的能问是什么东西非要在大年初一去买吗?况且这要求是老三媳妇提出来的,那更另当别论的。五叔从腰上解下一串钥匙,起身进了卧室。五叔很麻利地打开一口老掉牙的樟木箱子,捧出一只盒子来,拿出一叠钱,数了数,又返回身取了一些,大概凑了个整数。想给老三媳妇,大概觉得不合适,又把钱递给老大媳妇,说,这是你们几家每年给我的,我都存着呢。老大媳妇你拿着,到了城里,你们看好了什么就买。老大媳妇刚想推辞,老三媳妇给嫂子递了个眼色,谢谢爸爸!祝您老人家长命百岁!
但凡上了岁数的老人,都希望自己能越活越年轻,也愿意听到这样的祝福话。这一高兴,五叔回头喊,老四,给你嫂子们开车。老三媳妇忙说,不用了,老四昨晚睡得晚,把钥匙给我,我开车。老四正在电脑上玩游戏玩得不可开交,巴不得呢,扔过车钥匙,辛苦嫂子了。有媳妇在身边,总是受管制,抽支烟也要管着,老三朝媳妇做个鬼脸说,赶快去吧。媳妇瞪大眼睛,巴不得我走是不是?可别后悔。老三唱起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头——
四
妯娌四个出了门,上了车,便笑做一团。 老大媳妇说,这样行吗?
老三媳妇说,怎么不行?
老二媳妇说,我看这样行。
老四媳妇说,我看不行也行。
老大媳妇又说,说不定这样一来,老爷子就同意搬走了。
老三媳妇说,一个人住在乡下,整天让我们提心吊胆的。如果能达到这个效果,那真是中了头彩。四个媳妇又是一阵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互相捶打着,车子很快出了村子,飞上了公路。
五
几个媳妇都走了,家里立马安静下了。老大老二就陪着五叔说话,老四继续玩电脑游戏,老三与老大的儿子下起了象棋。陆续地,家里来了拜年的乡邻。老大老二就忙着给男客递烟,倒茶,说一些相互祝福的话。可是女客就没人招待了,老三要喊自家媳妇,猛然想起刚让人家“大胆地往前走,莫回头”来着,便只好自己动手了。
三个女人一台戏,这妯娌四个在一起,更有好戏看。都说妯娌在一起有矛盾,可五叔家这妯娌四个,却是难得的和谐。平时难得地聚在一起,这下子好了,可热闹了。先说了一通孩子的学习,又转到各自的服饰。老大老三媳妇是省城来的,自然要比老二老四媳妇时尚一些。于是她们俩就支招,明年冬天到城里买过年的衣服,别在这小县城买。老四媳妇就说,那我们去了你俩可得管吃管住啊。那当然,老三媳妇说,把你三哥撵走,你们俩就住我家,把大嫂再接过来,我们妯娌四个好好在一起疯两天。老四媳妇说,那我三哥还不得把我们俩恨个洞?舍得离开这么如花似玉的娘子?老三媳妇就搡了老四媳妇一把,去你的,都老夫老妻了,哪像你们,刚结婚,一夜折腾好几次吧?老四媳妇自然是要反击,于是妯娌四个乐得就差把车顶掀翻。
别吵,有情况!突然,老三媳妇用手势制止妯娌们的说笑,谁的手机响了?
老大媳妇说,是我的是我的,是老大的电话,接不接?
不接。老三媳妇说,等着吧,不出一分钟,二嫂的手机就要响。
果然,《月亮之上》的铃声格外清脆地响起来。老四媳妇说,二嫂的这歌我也会唱。“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
老三媳妇说,得了吧,老四,你那破锣嗓子,还唱。老四媳妇当然不让,大嫂二嫂你们看,三嫂总是和我过不去。回去告诉三哥,让三哥收拾你。哎呀,大嫂的手机又响了。凡是他们打的,一律不接,老三媳妇话还没说完,自己的手机叫起来,她连看也没看就模仿着老三早上的腔调唱起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呀头……
老四的手机也不甘寂寞,紧跟着“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雨(里格)绵绵,(介支个)秋风寒……”铃声挺缠绵也挺顽固,一直唱到“十送”,还不舍得停下。老三媳妇就说,看看,到底是年轻,这么粘人呢,有完没完啊。
就这样,妯娌四个的手机从九点半开始响,铃声此起彼伏。而她们几个,不接也不关机,就由着那铃声响个不停。每响一次,她们就挤眉弄眼一番。就像几个恶作剧的孩子,嘻嘻哈哈甚是开心。
这边四个女人死活不接手机,这下可苦了在家里的那四个大老爷们儿。他们一遍遍地打着自己老婆的手机,没有回音;又一遍遍地打着嫂子或弟妹的手机。一开始,他们以为在超市吵得慌,听不见也有可能。可是,到后来,四个大老爷们就犯了嘀咕,不会吧,不会四个人都没听见吧。就是呀。可是她们为什么不接呢?
五叔一如既往地留人吃饭,还说,不论大人孩子,一个也不能少。她们再不回来,这午饭可咋办?当初就不该答应她们出去,老三突然想起老婆临走时那句:你可别后悔。莫非她们几个早就串通好了不成?哎呀,上她当了!我这猪头脑子!
六
接近中午,媳妇们满载而归了。
走进院子,老大正铁着脸站在那里,像是特意等她们回来似的。一看媳妇回来了,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冲自家媳妇说,打电话怎么一个不接?什么什么?打我电话了?老大媳妇一脸的茫然,没听见啊。把你们手机拿出来自己看。四个人分别磨磨蹭蹭地从口袋里、皮包里摸出手机,按照路上安排好的:老大老四媳妇分别举着手机说,晕死,我的手机没电了呀。老二老三媳妇则一脸无辜,啊,这么多未接电话呀,超市吵死了,一个没听见。是呀是呀,在车上那音乐声又大,根本没听见呀。打我们电话有事吗?早知道有事我们就不去了。妯娌四个七嘴八舌地嚷嚷着,早把屋里的情景尽收眼底——屋里没有客人,五叔正闷闷地抽着烟,一言不发。
媳妇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突然觉得这个玩笑是不是开大了。
正月初三,我去给朋友拜年,碰到五叔,我说五叔你过年好啊。五叔说,不好,这个年过的不开心。随后又补充说是相当不开心,这是我在这里过得最后一个年了,开了春就去城里住了。我说您什么时候回来?五叔叹口气,所答非所问,你再租房子就住五叔这儿吧,宽敞,不要你房租,住多久都行。
作者简介:张力华,1965年生于山东平度,现工作于仪征广播电视台.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仪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散文集《让我轻轻告诉你》《谢谢有你》。
原文刊登在仪征杂志2010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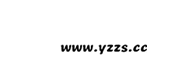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