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写字的仪城河
汪向荣 在枕江襟水的仪征小城生活,许多感受总与“滋润”有关,当然,我要表述的“滋润”,不只是悠然闲适的自足状态。从84年来到这座荷塘、河流密集的城市,从新河东路的商业仓库到鼓楼桥南的糙石巷,直至如今的镜湖花园,居所离城河从未超过50米,更确切地讲,这么多年我一直住在河岸上。城河,不离不弃,已陪了我1万多个日夜,给以“开窗终日鸟声闻”的耳福,给以“参天两岸树合荫”的美景,更给以“中有人家住绿云”的佳境。应当说,它是我真正的朋友,贴心知已的朋友,可我却常常把它冷落了,甚至背弃了,这样不仁不义者并非我一个,但在这里,我还是要向城河说一声:“对不起”。
对于被习以为常的母性水系拥抱着、宠爱着的居民而言,城河就是一条河,不管它是历史传承,不是自然造化,人工开凿,都不能改变“河”本身的属性——柔弱得扶不动,坚韧得撕不开,轻盈得聚不拢,固执得劝不走。人们更习惯将东西走向的城河作为这座城市的生活轴线,城北的人到城南上班、送孩子读书;城南的人到城北游园、逛街,两股人流就象波动的水体,总是早晨或者黄昏在桥上交汇。城河见证了他们的忙碌,也鉴照了他们的疲惫;城河接受过“四面柳荫遮不断,一船人行绿天中”的礼赞,也承受过烂腥腐臭、溺毙无辜儿童的诅咒和痛恶,但城河并不辩白,它从不轻易表达内心的感受。城河绝大多数状态表现为静谧、安宁,表现为遵纪、守法,不越“雷池”一步,在护坡石块、水泥栏杆的约束下,在被格式化的流程中,岸,成了自由的终极边界;岸,给河最大的自由莫过于让它沿着岸流淌,基于这样的背景,你会觉得河道就是静静的课堂,服从于威严的老师;水,就是专心致志的学生,倾听着这座城市的灌输:关于“风物淮南第一州”的荣耀;江淮盐运枢纽的昌盛;关于伍子胥、文天祥逃难过江的传奇;关于真州八景的来历,南门大码头的故事;以及四月绿茶、五月芍药的节俗;还有江淮方言、原味农歌……,有时为了一字不落地收听,城河会心灵手巧、异常娴熟地自制出一张张圆波的光盘,忠实地存储起那些海量的信息,它认为这些都值得秉烛夜读、认真复习;虽然城河在倾听时波澜不惊,但在它的身体内部,在人的视线无法企及的心灵深处,却总有着丰富的表达,每当听到“东南佳丽,天开图画”……这样的华丽语汇或“我爱你,谢谢你”的文明问候,它的分子会异常兴奋,结晶出美丽的六角形,而听到“×养的、滚一边去”之类的脏话,它的份子又会紧张收缩,露出痛苦的表情,这种不为人知的反应,是鱼儿告诉我的:在一个湿漉漉的梦中,鱼儿提醒岸上的人,对养育他们的水要友好一些、亲善一些、文明一些。当然城河有时也会厌烦冰冷无情、应试教育式的管制。只要大风一来,既有的秩序就会在一瞬间玉碎,叠叠波浪,前呼后拥,彼此拉扯,冲撞,狂喊着,随心所欲把积淀收藏了上百年的古城水墨泼洒得满岸都是,全无章法可言;岸,岂能容忍这样的撒野,就用圆弧状的挡浪墙盾牌般地将骤起的躁动压制下去,以前讲“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此时的“哗变”不过一刻钟就又归于平静,看来揭竿而起,敢作敢当,不是城河的秉性。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就没有几只惬意的游船,带着轻松的橹谣,领着浪花跟跑,徜徉在三月如画的城河里,给它带来音乐和健身的欢乐;我也不明白,充满女性魅力的仪城河,将早些年那些赤裸着上身,在盛夏里蛙游、狗爬,毫无顾忌的男人,放逐到了何处?现在,城河似乎就是城河,少了些生动的章节,静流似乎就是静流,不再有曲折的故事,谁也猜不透,城河究竟存在怎样的心思,谁也说不清,在读了那么多城市教给的历史、自然、人文、经济等浩繁的课程后,在摹临了那么多真州八景的古帖范本后,它想书写些什么?
就象前文描绘的,城河绝大多数时间的确是保持一种静默,但这不等于甘心寂寞,恰恰相反,它的体态一直那么丰盈、饱满,处于酝酿、孕育之中,这让人很轻易联想到注满墨水的胶囊,一种与书香、墨韵、写作紧密相关的神秘意象。作出这样的比喻,城河听了,一定很舒心,因为我相信这种比喻,更贴近它的品质和内心。在前辈的诗人眼里,它的好处固然在于观赏性——“最好城河水二分”,其实它真正给予整座城市的远不止此:1720年冬,知县李昭治主政,采纳民意,倾力疏浚,结果金秋丰收,十一人中举,人们感恩于水畅、政通、人和,从此将清淤当成惠及自己的事、造福他人的事,三五年不到就要为它“疏经活血”,为它将迎接“科举”的墨灌得满满的,磨得浓浓的。城河是书生通向显达,文人通向富贵的“举人河”。作好文章,应当是它的拿手好戏;过好日子,应当是它的由衷祝愿。
城河静默时,果真就象一支充满成功欲望的笔,无时不在对智慧之墨、生命之墨畅快地吸吮,从上游的河流,从比它更粗大的动脉之中。城河直接的上游是被石岸锁牢、柳堤护呵的石桥河,但石桥河不过是南北走向的简短过渡段落,它真正为城河联通的是与城河同样走向的仪扬运河,这是真正向城河输送丰沛基因,倾注活力骨髓,遗传情思才识的母体。仪扬运河顾名思义,是沟通扬州与仪征两座城市的运河,在历史上淮盐就是通过它强劲的脉动,向长江中下游中转分运的。在鼎盛时仪征(真州)发行的盐钞占全国的1/4,世界上最早的大型船闸就诞生在这里。你听说过“有京师,不可无真州”一说,就知道一条河对于一座城市,对于一个国家政权的重要。即便现在,仪扬运河,仍是我见过的最宽阔的河流,虽然它与市中心有3公里以上的距离,虽然它并不直接与市中心的城河发生关系,见过它的人都会为城郊流淌着这样一条大河而惊叹。它是大河,自有大河的胸怀和气魄,沿着长达26公里的大堤步行,高高的意杨、刺槐一路铺陈浓郁的绿意凉荫;又一路可见野鸡、野鸽的频繁出没,坡上的枸杞头、香椿头是它慷慨奉献给城市居民的自然馈赠,只要在三月头,拎着篮子去,准能满载而回。而从南岸到北岸,有大约百米的宽幅,它因此就有足够的容量将沿岸的风光清晰而全景地纳入镜框之中;她就有更大的气度接纳不知来处的脏污:垃圾袋、塑料瓶、残枝枯叶、死猪死猫死狗甚至人的浮尸,对此它忍受了羞辱并不懊恼,遭到了误读不急于“自清”, 它传给城河的脾气也是这样——只是静静地移动着丰满的水体。然而在淡定、从容的外表之下,在光滑细腻的皮肤之下,在夏日日见隆起的母腹之下,它也不隐藏内在的裂变,孕妇的胎动。只要有船,有来自里下河送煤炭、砂石的船出现,就会引起分娩式的强烈反应。有一天,接近黄昏,我站在一座运河大桥上拍照,然而总感到岸树、静水、夕阳的组合过于沉寂、单调,缺乏生动的元素,刚露出些许遗憾,刚留下一声叹息,运河,就看出了我的心思,运河,就懂得了我的需求。它善解人意,恰当其时,送来了一只船,一只弦帮紧贴着水面、装载甚重的船“突、突、突”地过来了,就象一把锋利的刀从水中央剪开一道粗大的口子,一道皮开肉绽的口子——这是船在给河做剖腹产:浪花诞生了,成群的浪花诞生了,她们一边发出“哗、哗”的啼哭,一边本能地拉扯着伴随母体一千年的土质岸线,雄性的岸线,父亲的岸线感动了,澎湃的心潮打湿了满脸,有几处浸泡得发软的土层很快被扯进水里——岸,有时也有脆弱的一面,这样短暂而神圣的生命孕育,让我得到了求之不得、婴儿般鲜活的镜头。但河却付出了巨大的阵痛,此时它显然闻到了血腥而温暖的气息正从上游吹来,那是源头的水正在为它输血,为它复元,而在下游许多白色的鸟群正逆风聚集于两河交汇处,为它默默地将新生命注入城河表示敬意。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平素神情平和的仪城河,有时会疾速奔流,显得十分暴躁,并裹杂着一大团散发着异味的漂浮物,原来是运河通过东门大闸向着城河分泄,落差形成的压力和流速,几乎一秒之间,就能将城河的水全面更新,这比风吹开一轮波纹,或翻动一张书页更为快捷,如此彻底的循环透析,对于面临“高血压”和肾病威胁的城河是必不可少的预防和“救赎”,也正因为如此,城河的舒坦流畅,城河的文思泉涌才表现得更为必然和充分,她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她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某天,当我看到一张仪征城市地图时,那蓝色的几根线条,看似孩子信手的几笔,却给了我一个意外的发现:原来,仪城河几百年来久酿于胸,渴望挥写的题目竟是一个“曰”字:仪城河、仪扬运河、长江由北向南,由细而粗的“三横”,石桥河、胥浦河笔直、遒劲的“两竖”,中间纵然留下一些看似断裂、貌似分离的飞白,整个字的走笔运势,仍不失清逸、灵动、淋漓,挺有“蚕头雁尾”隶书味道。当四月的一个晴天,当这个晴天的正午,我把这个发现说给城河听的时候,她用微微的风浪予以肯定,并用轻拂的杨柳和温暖的阳光表示感谢!
其实,我,不仅是我,整座城市都应感谢的是城河,感谢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为这座城写的那个“曰”字,感谢这个“曰”字所蕴藉的丰富内涵和良好祝愿。长江自不必讲,城河是文静的人文河,仪扬河是大爱的母性河,石桥河是纯粹的景观河,胥浦河是豪爽的英雄河(因渔丈人义救伍子胥而得名),这些不同的笔划,支撑起城市的内在骨架,而融会贯通,入江通海的开放体系,又在大地的宣纸上铺展着城市的外向气度,有哪座城市象这里,几乎有70%左右的居民就生活在河的两岸,生活在这些河流自觉、和谐共写的“曰”字之中。吃它煮的饭,食它浇的菜,品它滋养的红芍,喝它泡制的绿茶……过着“滋润”的日子,其实水系已不可阻挡地涌进我们的胸腔、浸润我们的内心,复制、缩写为殷红的血脉,一外一里,彼此呼应,人,在水中;水,在人中……,有一天,当我读到日本著名作家、医学博士江本胜的《水知道答案》时,几乎惊诧得目瞪口呆:“人类受精卵的99%是水;出生后,水占人体的90%;成人后,这一比例减到70%,临死前降到50%”,“水本身是可以复制信息,加以记忆,并表达美好情感的生命”……。而在此之前,我对水的认识极为浅薄,甚至无知。
现在,春天正引领大地向绿意深处走去,住在离城河50米左右的我,住在离城河不远的人们,更喜欢到河滨散步,对于这样的亲热,对于这样的贴近,城河很欢迎,城河并不计较与它疏远、甚至污染过它的人们有无对它说声“对不起”,道声“谢谢你”。城河只是说,人,本身就是水做的,除了河,他能流到哪里? 2010年4月25日于仪征
作者简介:汪向荣,男,1966年生于泰兴。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扬州市作家协会理事,仪征市作家协会主席,原《仪征日报》社总编。著有诗集《石榴之忆》,文集《仪征,走进你的心灵》等;省青创会、作协代表。诗作入选《江苏50年诗选》、“中国江南才子派诗展”。
汪向荣 在枕江襟水的仪征小城生活,许多感受总与“滋润”有关,当然,我要表述的“滋润”,不只是悠然闲适的自足状态。从84年来到这座荷塘、河流密集的城市,从新河东路的商业仓库到鼓楼桥南的糙石巷,直至如今的镜湖花园,居所离城河从未超过50米,更确切地讲,这么多年我一直住在河岸上。城河,不离不弃,已陪了我1万多个日夜,给以“开窗终日鸟声闻”的耳福,给以“参天两岸树合荫”的美景,更给以“中有人家住绿云”的佳境。应当说,它是我真正的朋友,贴心知已的朋友,可我却常常把它冷落了,甚至背弃了,这样不仁不义者并非我一个,但在这里,我还是要向城河说一声:“对不起”。
对于被习以为常的母性水系拥抱着、宠爱着的居民而言,城河就是一条河,不管它是历史传承,不是自然造化,人工开凿,都不能改变“河”本身的属性——柔弱得扶不动,坚韧得撕不开,轻盈得聚不拢,固执得劝不走。人们更习惯将东西走向的城河作为这座城市的生活轴线,城北的人到城南上班、送孩子读书;城南的人到城北游园、逛街,两股人流就象波动的水体,总是早晨或者黄昏在桥上交汇。城河见证了他们的忙碌,也鉴照了他们的疲惫;城河接受过“四面柳荫遮不断,一船人行绿天中”的礼赞,也承受过烂腥腐臭、溺毙无辜儿童的诅咒和痛恶,但城河并不辩白,它从不轻易表达内心的感受。城河绝大多数状态表现为静谧、安宁,表现为遵纪、守法,不越“雷池”一步,在护坡石块、水泥栏杆的约束下,在被格式化的流程中,岸,成了自由的终极边界;岸,给河最大的自由莫过于让它沿着岸流淌,基于这样的背景,你会觉得河道就是静静的课堂,服从于威严的老师;水,就是专心致志的学生,倾听着这座城市的灌输:关于“风物淮南第一州”的荣耀;江淮盐运枢纽的昌盛;关于伍子胥、文天祥逃难过江的传奇;关于真州八景的来历,南门大码头的故事;以及四月绿茶、五月芍药的节俗;还有江淮方言、原味农歌……,有时为了一字不落地收听,城河会心灵手巧、异常娴熟地自制出一张张圆波的光盘,忠实地存储起那些海量的信息,它认为这些都值得秉烛夜读、认真复习;虽然城河在倾听时波澜不惊,但在它的身体内部,在人的视线无法企及的心灵深处,却总有着丰富的表达,每当听到“东南佳丽,天开图画”……这样的华丽语汇或“我爱你,谢谢你”的文明问候,它的分子会异常兴奋,结晶出美丽的六角形,而听到“×养的、滚一边去”之类的脏话,它的份子又会紧张收缩,露出痛苦的表情,这种不为人知的反应,是鱼儿告诉我的:在一个湿漉漉的梦中,鱼儿提醒岸上的人,对养育他们的水要友好一些、亲善一些、文明一些。当然城河有时也会厌烦冰冷无情、应试教育式的管制。只要大风一来,既有的秩序就会在一瞬间玉碎,叠叠波浪,前呼后拥,彼此拉扯,冲撞,狂喊着,随心所欲把积淀收藏了上百年的古城水墨泼洒得满岸都是,全无章法可言;岸,岂能容忍这样的撒野,就用圆弧状的挡浪墙盾牌般地将骤起的躁动压制下去,以前讲“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此时的“哗变”不过一刻钟就又归于平静,看来揭竿而起,敢作敢当,不是城河的秉性。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就没有几只惬意的游船,带着轻松的橹谣,领着浪花跟跑,徜徉在三月如画的城河里,给它带来音乐和健身的欢乐;我也不明白,充满女性魅力的仪城河,将早些年那些赤裸着上身,在盛夏里蛙游、狗爬,毫无顾忌的男人,放逐到了何处?现在,城河似乎就是城河,少了些生动的章节,静流似乎就是静流,不再有曲折的故事,谁也猜不透,城河究竟存在怎样的心思,谁也说不清,在读了那么多城市教给的历史、自然、人文、经济等浩繁的课程后,在摹临了那么多真州八景的古帖范本后,它想书写些什么?
就象前文描绘的,城河绝大多数时间的确是保持一种静默,但这不等于甘心寂寞,恰恰相反,它的体态一直那么丰盈、饱满,处于酝酿、孕育之中,这让人很轻易联想到注满墨水的胶囊,一种与书香、墨韵、写作紧密相关的神秘意象。作出这样的比喻,城河听了,一定很舒心,因为我相信这种比喻,更贴近它的品质和内心。在前辈的诗人眼里,它的好处固然在于观赏性——“最好城河水二分”,其实它真正给予整座城市的远不止此:1720年冬,知县李昭治主政,采纳民意,倾力疏浚,结果金秋丰收,十一人中举,人们感恩于水畅、政通、人和,从此将清淤当成惠及自己的事、造福他人的事,三五年不到就要为它“疏经活血”,为它将迎接“科举”的墨灌得满满的,磨得浓浓的。城河是书生通向显达,文人通向富贵的“举人河”。作好文章,应当是它的拿手好戏;过好日子,应当是它的由衷祝愿。
城河静默时,果真就象一支充满成功欲望的笔,无时不在对智慧之墨、生命之墨畅快地吸吮,从上游的河流,从比它更粗大的动脉之中。城河直接的上游是被石岸锁牢、柳堤护呵的石桥河,但石桥河不过是南北走向的简短过渡段落,它真正为城河联通的是与城河同样走向的仪扬运河,这是真正向城河输送丰沛基因,倾注活力骨髓,遗传情思才识的母体。仪扬运河顾名思义,是沟通扬州与仪征两座城市的运河,在历史上淮盐就是通过它强劲的脉动,向长江中下游中转分运的。在鼎盛时仪征(真州)发行的盐钞占全国的1/4,世界上最早的大型船闸就诞生在这里。你听说过“有京师,不可无真州”一说,就知道一条河对于一座城市,对于一个国家政权的重要。即便现在,仪扬运河,仍是我见过的最宽阔的河流,虽然它与市中心有3公里以上的距离,虽然它并不直接与市中心的城河发生关系,见过它的人都会为城郊流淌着这样一条大河而惊叹。它是大河,自有大河的胸怀和气魄,沿着长达26公里的大堤步行,高高的意杨、刺槐一路铺陈浓郁的绿意凉荫;又一路可见野鸡、野鸽的频繁出没,坡上的枸杞头、香椿头是它慷慨奉献给城市居民的自然馈赠,只要在三月头,拎着篮子去,准能满载而回。而从南岸到北岸,有大约百米的宽幅,它因此就有足够的容量将沿岸的风光清晰而全景地纳入镜框之中;她就有更大的气度接纳不知来处的脏污:垃圾袋、塑料瓶、残枝枯叶、死猪死猫死狗甚至人的浮尸,对此它忍受了羞辱并不懊恼,遭到了误读不急于“自清”, 它传给城河的脾气也是这样——只是静静地移动着丰满的水体。然而在淡定、从容的外表之下,在光滑细腻的皮肤之下,在夏日日见隆起的母腹之下,它也不隐藏内在的裂变,孕妇的胎动。只要有船,有来自里下河送煤炭、砂石的船出现,就会引起分娩式的强烈反应。有一天,接近黄昏,我站在一座运河大桥上拍照,然而总感到岸树、静水、夕阳的组合过于沉寂、单调,缺乏生动的元素,刚露出些许遗憾,刚留下一声叹息,运河,就看出了我的心思,运河,就懂得了我的需求。它善解人意,恰当其时,送来了一只船,一只弦帮紧贴着水面、装载甚重的船“突、突、突”地过来了,就象一把锋利的刀从水中央剪开一道粗大的口子,一道皮开肉绽的口子——这是船在给河做剖腹产:浪花诞生了,成群的浪花诞生了,她们一边发出“哗、哗”的啼哭,一边本能地拉扯着伴随母体一千年的土质岸线,雄性的岸线,父亲的岸线感动了,澎湃的心潮打湿了满脸,有几处浸泡得发软的土层很快被扯进水里——岸,有时也有脆弱的一面,这样短暂而神圣的生命孕育,让我得到了求之不得、婴儿般鲜活的镜头。但河却付出了巨大的阵痛,此时它显然闻到了血腥而温暖的气息正从上游吹来,那是源头的水正在为它输血,为它复元,而在下游许多白色的鸟群正逆风聚集于两河交汇处,为它默默地将新生命注入城河表示敬意。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平素神情平和的仪城河,有时会疾速奔流,显得十分暴躁,并裹杂着一大团散发着异味的漂浮物,原来是运河通过东门大闸向着城河分泄,落差形成的压力和流速,几乎一秒之间,就能将城河的水全面更新,这比风吹开一轮波纹,或翻动一张书页更为快捷,如此彻底的循环透析,对于面临“高血压”和肾病威胁的城河是必不可少的预防和“救赎”,也正因为如此,城河的舒坦流畅,城河的文思泉涌才表现得更为必然和充分,她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她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某天,当我看到一张仪征城市地图时,那蓝色的几根线条,看似孩子信手的几笔,却给了我一个意外的发现:原来,仪城河几百年来久酿于胸,渴望挥写的题目竟是一个“曰”字:仪城河、仪扬运河、长江由北向南,由细而粗的“三横”,石桥河、胥浦河笔直、遒劲的“两竖”,中间纵然留下一些看似断裂、貌似分离的飞白,整个字的走笔运势,仍不失清逸、灵动、淋漓,挺有“蚕头雁尾”隶书味道。当四月的一个晴天,当这个晴天的正午,我把这个发现说给城河听的时候,她用微微的风浪予以肯定,并用轻拂的杨柳和温暖的阳光表示感谢!
其实,我,不仅是我,整座城市都应感谢的是城河,感谢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为这座城写的那个“曰”字,感谢这个“曰”字所蕴藉的丰富内涵和良好祝愿。长江自不必讲,城河是文静的人文河,仪扬河是大爱的母性河,石桥河是纯粹的景观河,胥浦河是豪爽的英雄河(因渔丈人义救伍子胥而得名),这些不同的笔划,支撑起城市的内在骨架,而融会贯通,入江通海的开放体系,又在大地的宣纸上铺展着城市的外向气度,有哪座城市象这里,几乎有70%左右的居民就生活在河的两岸,生活在这些河流自觉、和谐共写的“曰”字之中。吃它煮的饭,食它浇的菜,品它滋养的红芍,喝它泡制的绿茶……过着“滋润”的日子,其实水系已不可阻挡地涌进我们的胸腔、浸润我们的内心,复制、缩写为殷红的血脉,一外一里,彼此呼应,人,在水中;水,在人中……,有一天,当我读到日本著名作家、医学博士江本胜的《水知道答案》时,几乎惊诧得目瞪口呆:“人类受精卵的99%是水;出生后,水占人体的90%;成人后,这一比例减到70%,临死前降到50%”,“水本身是可以复制信息,加以记忆,并表达美好情感的生命”……。而在此之前,我对水的认识极为浅薄,甚至无知。
现在,春天正引领大地向绿意深处走去,住在离城河50米左右的我,住在离城河不远的人们,更喜欢到河滨散步,对于这样的亲热,对于这样的贴近,城河很欢迎,城河并不计较与它疏远、甚至污染过它的人们有无对它说声“对不起”,道声“谢谢你”。城河只是说,人,本身就是水做的,除了河,他能流到哪里? 2010年4月25日于仪征
作者简介:汪向荣,男,1966年生于泰兴。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扬州市作家协会理事,仪征市作家协会主席,原《仪征日报》社总编。著有诗集《石榴之忆》,文集《仪征,走进你的心灵》等;省青创会、作协代表。诗作入选《江苏50年诗选》、“中国江南才子派诗展”。
原文刊登在仪征杂志2010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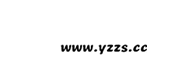

网友评论